五月了,以前曾經是我理所當然最喜歡的月份。這些年卻多了一些複雜的心情。
就在前幾天天氣逐漸暖起來,似乎要正式邁入夏天時,卻讀到一本冰天雪地的小說。三十幾歲還沒結婚的,在事務所工作的,一個人外派他鄉的。
《Snowdrops 雪墜》(A.D. Miller, 2011 英國曼布克獎入圍)
尼克拉斯是一個外派在莫斯科工作的英國律師,38 歲。他們的法律事務所負責替跨國銀行審閱在俄羅斯的投資計劃中,申貸公司提出的產權、投資權利等法律文件,以及在投資計劃核准後準備銀行放貸所需的法律文件。
莫斯科的冬天開始得很早,但那時才九月,還是能開著窗戶吃晚餐的時節。有一天在地鐵站,尼克遇到一宗搶劫,歹徒搶一個女孩子的包包拽倒了她就要跑,尼克拉斯於是見義勇為給了歹徒一拳,雖然沒把人當場逮住,倒還有把包包搶回來。女孩跟她的妹妹向他道謝。
如果他笑笑說聲沒什麼,然後英雄式地轉身離開,也許事情就會完全不同吧。
但他停了下來。看著她美麗的,微笑的眼睛……他們相視而笑太久了,得要有人說句話吧,於是她用英文問他從哪兒來。就這樣,他認識了美麗的瑪莎,和她妹妹卡蒂雅。
尼克跟瑪莎就這樣開始約會了。瑪莎在一家通訊行當店員賣手機,卡蒂雅還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念書。她們是 24 歲跟 20 歲,來自摩曼斯克,俄國在北極圈內靠近挪威和芬蘭的小城。她們在莫斯科沒有其他親戚,只有一位伯母,一個人住在市中心。
也許就是那一陣子吧,他注意到他家巷口,那台舊芝古力好像停了一陣子了,俄國國產車,夾在兩輛 BMW 中間。那是在共產時期每個俄羅斯男人夢想中的車。直到開放之後,他們才知道他們連作夢都夢得比美國人寒傖。
瑪莎和他約會了一陣子,他們每星期見個兩三次面。他們聊倫敦和莫斯科的種種不同,聊他的爸爸曾在大戰期間運補到摩曼斯克港口,而她的爺爺則是在港口駕駛破冰船,想想說不定他們倆的父祖那時曾合作過呢。
他們在大街上的迷離光影裡散步,到河邊的餐廳吃飯,到他家坐坐,上床。
他愛上她了。他的記者朋友說,「那她有說她愛你嗎?」呃,還沒有。
十月十一月,冬天開始了。雪開始堆積。深夜三點,穿著亮橘色的除雪大隊在雪堆上灑除凍劑,然後用機具把雪鏟到路邊,路邊不管剛好停什麼車,例如那台倒楣的芝古力,就會被埋在雪堆底下。半夜三四點的狂暴剉冰聲實在惱人,但尼克不會埋怨他們,他知道他純粹是出於幸運,才會是半夜在溫暖的被窩裏被吵醒,而不是半夜三四點得在天寒地凍中在路邊鏟雪的人。
瑪莎她們不時會去看看她們的伯母,就問他要不要一起去,跟伯母見個面。那當然好啊。
伯母熱情地準備了一桌大餐,傳統的俄羅斯料理,吃得他簡直太撐了。她談她過世的先生,談他從前是對國家有傑出貢獻的科學家,所以國家配給他市中心的房子。談他們曾有過的美好時光。然而,現在只剩她一個人住在這間房子裡了。
尼克手邊這個在裏海旁邊投資供油槽的案子挺大的,申貸方的公司負責人政商關係很不錯的,前 KGB,現在改叫 FSB 聯邦安全局的人。他們事務所也請了獨立的現場調查員來,負責觀察油槽設備的進口及設置施工情形,再按投資計畫的進度建議銀行分批撥款。這個案子將是近年最大的貸款案。
和英國報紙駐莫斯科的記者朋友喝酒的時候,尼克拉斯問,「要是你你會把這個案子寫成怎樣的故事 / 新聞 (story)?放商業版?政治版?」
他的記者朋友點了根菸,說,「在俄羅斯,沒有所謂的商業故事,沒有所謂的政治故事。甚至沒有所謂的愛情故事。只有犯罪故事。」
尼克拉斯回家時,鄰居歐雷格在門口等他,老歐雷格說他的朋友康士坦丁不見幾天了,請尼克幫忙找找。康士坦丁的家就住在隔壁街。尼克心想,康士坦丁可能在家睡了,可能路倒了,可能去哪兒了。但拗不過擔心的歐雷格,他還是去了那條街去他家敲敲門,跟附近鄰居問問,也到警察局報了案。
十二月,雪越來越大了。大雪將市景裏一切尖銳的角度鈍化,將所有不堪的景象都用白皚皚掩蓋起來。
「尼古萊,」瑪莎說,「你是律師嘛,能不能幫我伯母一個忙。她在考慮跟人交換房子,搬去郊區住。你可不可以當他的法律代理人,幫她搞定法律上的東西。」換屋是共產時代的遺緒,住房是國家配給你的,所以不能賣了換錢,不過你倒可以跟人以屋易屋;後來實施市場經濟了,許多人仍然是以換屋的方式在交易,也許再補一些差價。
瑪莎兩姐妹和他陪著伯母,四個人一道去看了那間郊區的公寓。在地鐵的幾乎末站了。房子還沒完全蓋好,裸露的管線,還不能用的電梯,但是從他們的樓層可以看見結冰的湖,和薄霧裡教堂的塔尖。
伯母站在陽台眺望著,靜靜地看了很久。尼克問她:「喜歡嗎?」
「好。換吧。」那麼,他們只要跟此地的屋主雙方都準備好文件,等過幾個月房子蓋好,就可以正式換屋了。
跨年夜在伯母家慶祝。用過伯母精心準備的大餐之後,他們隨著收音機歡樂的音樂,在客廳跳起舞來,多半時候是尼古萊帶著瑪莎旋轉著,卡蒂雅帶著伯母。
伯母的神采彷彿仍是那個二十多歲剛嫁給年輕科學家的俄羅斯少女,飛揚著,大笑著。
午夜,紅場的煙火燦爛地施放起來,他們靜靜地看著煙火,瑪莎偎在尼克的身邊。他們四個人一起舉杯互祝新年快樂。她說:「尼古萊,我愛你。」
他想娶她,想帶她回倫敦。外派歸國,他升合夥人的時候正好可以向她求婚。
一月二月,溫度恆低於零下二十七八度。天寒地凍中隨著油槽設備的採購進口及工程進度,經過尼克跟他的主管審核過文件及現場調查報告之後,銀行也逐步撥款。
尼克老是在門口遇到歐格雷請他幫忙找康士坦丁,他還能幫什麼忙呢,他甚至也找了私家偵探,但警察是暗示他要拿出一點錢來辦事嗎,這他可辦不到。總之,沒消息。
尼古萊倒是有一回遇到卡蒂雅,在餐廳打工,不是快考試了嗎。聊到她和瑪莎在摩曼斯克的童年時,她說,「喔,你誤會了。我們叫 sister 不是那個同父母的姐妹,我不知道英文裡叫什麼。」「所以妳跟她應該是叫做 cousin,在英文裏,堂表兄弟姐妹都叫 cousin。」
他們有幾次和伯母一起去滑雪地度假,有一回,則是只有他和她們姐妹去溫泉度假。在熱騰騰的溫泉泡了一陣子之後,暖呼呼地起身,奔到戶外往鬆軟的積雪上一躺!哇,真是太過癮了,然後在冷掉到凍僵之前趕緊跑回溫泉浴室,他們尖叫著笑著……
三月了,伯母的新房子蓋得有一些進度,但不多。另外,因為在市中心的房子比較值錢,所以他們談定了對方得要再貼五萬美元給伯母(很特別地,在這種時候他們還是喜歡以美元訂合約)。若不是尼克跟瑪莎的堅持,伯母倒是覺得錢無所謂。
四月了,漸融的冰水在街道上漫流,混了泥沙和煙塵,像是沒端好灑了的烏梅雪泥一樣弄得到處都是髒污污的。
尼克拉斯又去敲了幾次康士坦丁的門,有一次,居然還有他的姪子出來應門,不過他也不知道康士坦丁去了哪裡。伯母的房屋交易倒是出了一點狀況:對方籌不出五萬美元來,只拿得出兩萬五,打算欠著伯母以後再慢慢還。
瑪莎說,「尼古萊,你可以幫這個忙嗎?這傢伙要是欠著伯母的話,伯母一個老人家去跟他討恐怕就討不到了。你可不可以借他兩萬五讓他有錢付給伯母,他欠著你的話是欠一個外國人,又是大律師,諒他不敢不還錢。」好吧。兩萬五。
這時,他作為伯母的法律代理人,也把伯母這邊需要提出的法律文件:產權證明、政府無拆除計劃證明、無他項權利設定證明、無其他權利人證明等等,都已經準備好了。
甚至他們還陪著伯母到醫院完成了精神狀態證明。
於是他們跟對方約好時間一同到銀行去簽約並提存那五萬美元。但在去簽約之前,瑪莎跟伯母說:
「伯母,尼古萊發現一個問題,就是法律上如果妳是用舊屋換新屋加五萬美元的話,國稅局會拿新屋加五萬來評定妳的舊屋價值,這樣妳就得補繳很多房產稅。這樣算一算不只那五萬美元沒了,還得多繳好幾十萬盧布。」伯母看著他,她不懂法律,但她信任他。
但他……他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件事。他後來查了之後稅法上並非如此,但當時聽起來好像是正確的。但他不懂,瑪莎為什麼會這麼說。
解決之道呢,瑪莎說,就是把換屋拆成賣屋跟買屋兩份合約,我們先簽賣的。「那什麼時候簽我買的那個新房子的呢?」伯母問。
「很快,」她說,「很快就簽。」
於是他們就先簽賣屋約吧。銀行說,那麼就算是成交了,恭喜。等房屋過戶完成,伯母就可以來銀行提領這五萬元。
他的工作上也有狀況,關於裏海油槽的投資計劃,跨國銀行準備要撥最後一筆,也是最大一筆款了,但是他主管和他去跟申貸方開會,看著這個現場調查員的報告說進口的設備都已運抵港口,油槽只要一完工,每日可供油數萬桶云云,總覺得哪裡不大對。但都走到這個時候了,要建議銀行中止撥款嗎?已經撥貸的部份呢?
他們把紅酒乾了,簽了報告建議銀行可以撥款。
過了幾天,尼古萊一個人去看伯母。她已經在打包準備搬家了。住了幾十年呢。
他忽然想知道瑪莎在摩曼斯克的童年,就問伯母。
伯母卻說,「她們……她們不是我的親人啊。」
啊?那她們是…?
「說來也滿特別的,我有一回搭地鐵實在提太多東西了,她們跟我同一站下車,就很好心幫我提回家裡來。」她不是她們的伯母。不是俄語裏的伯母,不是英語裏的伯母。不是任何語言裏的伯母。
尼克拉斯回家的路上,經過失蹤的康士坦丁家的那條街時,見到有人從康士坦丁家走出來。他楞了一下,發現那人卻不是那天他見到的那個姪子了。
在尼克拉斯家樓下的大門口,歐雷格老先生仍然愁容滿面站在門外看著街景。雖然現在他已經不再央請尼克幫忙找康士坦丁了。
六月初,康士坦丁終於開始發臭了。
尼克回家的時候。先是那個氣味,然後遠遠就看到人群圍觀,一走近他先看到的是有點變綠的腳,彷彿要下車似地,伸出在那台雪融之後終於重見天日的芝古力車門外……
他站到難過的歐雷格旁邊。歐雷格低垂著頭沒有看他,只說:警察說,康士坦丁是自殺的。朝自己的頭開槍。兩槍。
他對歐雷格感到很抱歉,想著自己是不是當初該多做些什麼。他找他的記者朋友談談這是怎麼回事。記者說,你朋友的朋友這種情況,在俄羅斯他們叫雪墜 (snowdrop),倒在雪裡的醉漢、遊民,或是被害人。就在大家眼前沒多遠的屍首,要到隔年春天以後,才會隨著融雪被發現。或者永遠不會被發現。
有跟人結怨嗎?或者他有房產?有房子可能就是一個原因。依俄羅斯法律,他如果失蹤五年之後就可以聲請法院判定他死亡。如果能證明他是在危險的狀況下失蹤,例如有目擊者作證看到他在嚴寒中落河、獨自在雪地裡行走等等,六個月就可以聲請判定死亡。
五年,甚至用不了五年,只要六個月。就會有繼承人冒出來。
需要證明文件?你沿著莫斯科的某條街走,從街頭走到街尾時,你已經可以從任何一所大學畢業、考上醫師執照、甚至證明你有能力發射飛彈。有些甚至是「真的」假證件,由真正的國家機構所發出,只是透過貪污的公務員而已。
而他們很快就會把房子再轉手出去,甚至在他們真正拿到手之前。
尼克心中也許早也知道事情不太好,但他沒想到會這麼壞。
從一起去銀行那次之後,他一直打不通瑪莎的電話,一開始還只是未開機轉語音信箱,到後來話筒則是直接傳回撥號錯誤的短促嘟嘟聲。他趕去伯母家,應門的人說從來沒見過或聽過他所說的人,或是當初要換屋的那個對方。
多虧了他依專業準備的法律文件,房子的過戶毫無問題。
他只能瞥見門後傢俱擺設都已不同,只剩下地磚依舊,他們曾在上面開心跳過舞慶祝新年的那片舊式地板。
他搭地鐵到幾乎末站到郊區的那棟公寓去,在樓下按了什麼門鈴都沒辦法找到人幫忙開樓下大門。甚至他懷疑門鈴的電線到底接起來沒有。他走到遠處,遠眺伯母曾在那裡看著教堂塔尖的陽台,想找到一點點有人入住的跡象。
沒有任何跡象,那個陽台沒有。那棟樓的任何陽台都沒有。
附近鄰居既沒聽過新屋主也沒聽過原屋主,只說,那棟樓啊,建商蓋不下去了,而且政府準備要徵收它要拆掉了吧。
他到瑪莎的通訊行去,她已經離職了。他到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商學院去,見到男女學生就問有沒有人認識卡蒂雅,雖然他知道卡蒂雅這輩子可能都沒有踏進過這所大學。他常到伯母家的附近。他想著也許他會再見到伯母,也許伯母會拿著那五萬元到他的辦公室來找他。
他的案子也黃了。所謂政商關係良好的申貸人不見了。FSB 的辦公室說從來沒聽過這個人。現場調查員也不見了。尼克拉斯和他的主管搭飛機轉計程車到裏海邊的油槽廠。沒有路了,計程車不願再開進去,他們只好下車,徒步拎著外套走了半個小時,走到那個地點。
沒有油槽、沒有油管、沒有可以日產萬桶或是任何一桶的任何東西。
他的主管直接被遠端開除。他被調回倫敦,調到做 Due Diligence 的部門,在標的公司的地下室負責啃文件,不用再跟客戶有任何接觸。
在調回倫敦之前,他還是常常到伯母家的附近。他常在市區閒逛,希望能偶然地瞥見伯母。或是卡蒂雅。或是瑪莎。
回到倫敦多年,他還是會想念雪夜裡那條大街上的迷離光影。想念瑪莎。想念莫斯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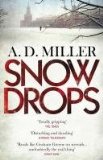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 我的部落格蒐藏
我的部落格蒐藏 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